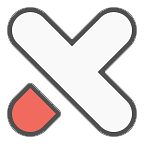黏菌-无脑的记忆
- 走进科学
- 2025-07-16
- 532热度
冠疫情期间,有些人开始烘焙,有些人决定养狗;而我则选择培养和观察黏菌。我伴侣在爱丁堡的公寓里的书房里,种着两种多头绒泡菌(Physarum polycephalum),这是一种无细胞黏菌,有时也被更随意地称为“黏菌团”。
我开始了一系列实验,研究从同一个切开的绒泡菌细胞中分离出的两个细胞团在重新引入后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停止融合。几个小时变成了几天,几天变成了几周,由于时间限制,实验最终在六周左右就失败了。然而,这仅仅是个开始。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我们毫无戒心的邻居并不知道),我又进行了几个实验。虽然这些实验都没有发表,但每个实验都启发了新的哲学问题——这些问题至今仍在影响着我的思考。其中一个核心问题是:黏菌的行为能告诉我们关于生物记忆的什么?
多头粘菌与人类之间的差异看似巨大,但黏菌却能揭示大量关于我们记忆方式的诸多方面。许多人可能认为我们的记忆主要储存在大脑中,但像我这样的一些哲学家认为,记忆——以及认知的其他一些方面——可以超越身体的局限,涉及与环境结构的耦合互动。简而言之,至少我们的部分认知过程会延伸到我们的周围环境中。黏菌是探索这一想法的一个有趣的候选对象,因为它根本没有大脑,但在某些情况下,它似乎可以“记住”事物,而无需将相关记忆储存在自身内部。在其他情况下,一个个体通过学习获得的记忆甚至可以通过身体接触被另一个个体获得。这种奇特生命形式的行为表明,我们关于记忆如何获得的一些观点可能需要重新思考。
磷多头绒泡菌(hysarum polycephalum)是一种团状生物,属于粘菌纲(Myxomycetes),也被称为“无细胞黏菌”。与细胞黏菌不同,细胞黏菌是单细胞的微型变形虫,在饥饿时会聚集在一起,形成巨大的蛞蝓状聚集体。绒泡菌由一个巨大的巨细胞构成 。它拥有复杂的生命周期,包含两个不同的营养生长阶段:微观的“变形鞭毛虫阶段”(孢子萌发后出现)和宏观的“原生质体阶段”。后者形态类似亮黄色、带有纹理的油漆溢出,已成为实验研究的主要焦点。这不仅是因为它惊人的体型(面积可达2平方米),还因为它惊人的快速运动速度——高达每小时5厘米。对于一个团状生物来说,这速度可谓相当不错。

它通过内部脉状小管的振荡收缩在细胞表面移动,这些小管将原生质重新分配到细胞边缘,形成类似扁平黄色花椰菜状结构的突起。在原体阶段,绒泡菌会积极地以微生物和腐烂物质为食,这两种食物来源在其自然栖息地——林地和森林地被中很容易获得。在那里,绒泡菌在潮湿的落叶、腐木和树桩中茁壮成长,向食物来源移动并包裹食物来源,同时避免阳光直射和干燥的表面。
绒泡菌可以通过优化其原生质管网络找到穿过迷宫的最短路径
在科学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绒泡菌(Physarum)被错误地归类为真菌,主要是因为它能够在带柄的子实体中产生孢子,类似于真菌的产孢结构。它的种名多头菌(polycephalum),字面意思是“多头”,指的是其子实体中多个孢子囊结构,表面上类似于微小的头部。然而,20世纪70年代的超微结构研究以及随后20世纪后期的分子系统发育学研究揭示,无细胞黏菌实际上属于变形虫纲(Amoebozoa),这是一类单细胞原生生物,与变形虫的关系比与真菌的关系更密切。
20 世纪 70 和 80 年代,人们对黏菌的兴趣高涨,欧洲、美洲和日本的实验室都开始研究它的行为。然而,到了20 世纪后期,研究开始下降。日本是一个重要的例外,那里对黏菌的研究仍在继续,并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发现。2000 年,中垣俊之发现了黏菌可以通过优化食物源之间的原生质管网络找到穿过迷宫的最短路径。最初,疟原虫会扩散,通过迷宫中的多条路径连接食物源。然而,它会选择性地收缩低效的路径,只留下最短和最有效的路线。这项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研究重新激起了全球对黏菌行为的兴趣,引发了对黏菌解决 问题和学习能力的研究热潮。
这一复兴的重要部分由法国的奥黛丽·杜苏图尔(Audrey Dussutour)以及澳大利亚的塔尼娅·拉蒂(Tanya Latty)、玛德琳·比克曼(Madeleine Beekman)和克里斯·里德(Chris Reid)等研究人员引领。他们开始开展有针对性的实验,研究绒泡菌(Physalum) 非凡的适应性决策能力、解决迷宫问题的能力,甚至表现出习惯化——一种简单的学习形式。曾经濒临被遗忘的绒泡菌,如今已被公认为行为生物学中一种有价值的模式生物。一些研究人员甚至将其作为非传统计算机进行探索,展示其如何执行处理任务并模拟电子元件。
但是像黏菌这样看似简单的生物怎么能记住呢?
西无论迁徙到哪里,绒泡菌都会留下细胞外黏液痕迹——一种非生物黏多糖。在野外,黏菌最常在食物匮乏的区域发现这些痕迹。原则上,遇到这些痕迹可以告诉黏菌该地区食物的可用性——但细胞外黏液是否被用作记忆痕迹呢?
为了探究这种可能性,2012年,生物学家克里斯·里德(Chris Reid)及其同事进行了一项颇具创意的实验。他们采用了两种不同的实验条件。在第一个“空白”条件下,他们在培养皿中铺上未经处理的琼脂,并在其上滴入一滴高浓度葡萄糖溶液——作为“目标”。扩散的葡萄糖溶液形成了一种吸引力梯度,黏菌可以沿着这一梯度向食物源前进。然而,研究人员也在途中设置了一个障碍:在食物源和黏菌的“起点”之间放置了一个干燥的U形醋酸盐陷阱。黏菌无法在干燥表面上有效移动,因此与之前的迷宫实验一样,它必须找到绕过障碍物的最佳路线。在第二个“覆盖”条件下,实验设置相同,只是琼脂上覆盖了一层细胞外黏液——仿佛黏菌之前就在那里,只是把它留在了那里。
Reid 和同事假设,如果绒泡菌利用细胞外黏液作为先前探索过的、可能食物匮乏区域的记忆痕迹,那么在覆盖条件下遇到踪迹的疟原虫到达目的地所需的时间要比在空白条件下长得多。在野外,已经觅食并耗尽食物的区域的环境记录很有用:它会告诉绒泡菌去其他地方寻找。但在这个特殊的实验设计中,研究人员发现,用细胞外黏液完全覆盖琼脂表面会减慢导航速度,因为这种均匀覆盖的表面会使绒泡菌自身的黏液踪迹基本未分化,因此毫无用处。相比之下,空白表面上的疟原虫可以停留并使用它们自己独特的黏液踪迹,创建一个差异化的空间地图,使它们能够避免重新访问先前探索过的区域。
而这正是他们发现的。在覆盖条件下,疟原虫达到目标所需的时间比空白条件下的其他疟原虫长10倍。在这种情况下,细胞外黏液并没有真正帮助疟原虫,但它确实向研究人员表明,疟原虫正在利用它作为记忆痕迹。
一个在爱丁堡大学完成博士学位后,我和一位导师决定合著一篇论文,探讨这些发现是否支持延展认知假说 (HEC)——这是哲学家安迪·克拉克和大卫·查尔默斯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提出的一个概念。简而言之,HEC 认为认知过程并不总是局限于大脑内部运作,有时还可以跨越大脑、身体和环境结构。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例子包括使用智能手机存储和调用电话号码,或在纸上进行计算。从这个角度来看,认知可以跨越大脑、身体和世界。我们被 HEC 吸引有几个原因。除了与克拉克(他也是我的博士生导师)的共同联系之外,我也对认知的进化以及非神经元生物如何为理解动物的认知运作方式提供线索越来越感兴趣。重要且切中要点的是,如果细菌、纤毛虫和原生生物(完全缺乏神经元的生物)表现出学习、记忆和预期行为等能力,那么 HEC 传统上对大脑、身体和世界之间的认知传播的关注似乎过于狭隘。
Reid 的研究清晰地展现了记忆痕迹存在于环境中,生物体会利用这些痕迹来指导未来遇到的情况。通常,生物记忆被认为是一种内部的、依赖于经验的变化,这种变化可以在之后被回忆和运用。但在本研究中,绒泡菌利用黏液在食物匮乏的区域导航,展现了一种跨越身体和环境的空间记忆形式。就 HEC 而言,这确实是一个“不费脑筋”的事情。
就像人类可以使用手机或笔记本电脑进行记忆存储一样,黏菌也可以利用黏液
2013年的一项后续实验支持了这一解释。这一次,Reid的团队表明,避开细胞外黏液不仅仅是一种厌恶反射或固定反应。当将疟原虫放入Y形迷宫中,在它和它感知到的高营养食物源(蛋黄)之间放置细胞外黏液时,疟原虫会忽略黏液,穿过黏液获取食物。重要的是,这一结果表明,黏液作为一种记忆痕迹,可以被新的显著信息(例如高质量食物的存在)覆盖,这符合导航记忆的一项广泛接受的标准。导航记忆与其他认知能力一样,很可能是为了指导动态环境中的适应性行为而进化而来的。如果这种记忆无法在新信息面前被覆盖,就有可能使生物体陷入适应不良的常规行为。以绒泡菌为例,这意味着它会忽略可用的食物,因为它靠近通常贫瘠的黏液路径。食物的高品质也至关重要:这表明绒泡菌对黏液线索的推翻是一个综合的评估过程——类似于成本效益分析。记忆与简单的刺激-反应回路不同,它被整合到生物体更广泛的认知经济体系中。
正如人类可以利用手机或笔记本电脑来储存和回忆记忆一样,黏菌也能利用黏液。诚然,数字记忆和导航记忆的性质不同,但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在进化过程中,黏菌早在人类之前就偶然发现了一种外部记忆解决方案。
细胞外粘液可被任何与留下它的粘液菌密切相关的粘液菌用作记忆痕迹,这一事实也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这是谁的记忆?记忆痕迹通常被理解为通过依赖经验的学习而获得,并由获得它的同一个体拥有。然而,就绒泡菌而言,使用细胞外粘液的细胞和留下它的细胞可能会有所不同。这里有一种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如果留下粘液的疟原虫(或另一个密切相关的细胞)没有再次遇到并使用这种粘液,它就根本不能算是记忆痕迹。只有当疟原虫与细胞外粘液相互作用并使用细胞外粘液来导航和指导其未来行为时,才会产生记忆痕迹。因此,如果粘液可以算作记忆痕迹,那么这种记忆就属于遇到并使用它的那一种粘液菌。神经哲学家朱利安·基弗斯坦和我把这个过程称为“记忆生成”(memory making)。在外部空间记忆中,记忆的存储和回忆紧密相连。相比之下,通过学习获得并储存在生物体内的记忆痕迹,并不依赖于生物体是否使用它来构成(自身的)记忆。
西黏菌记忆之所以如此有趣,是因为——至少在某些情况下——它似乎不需要通过直接经验来学习,而当我们考虑自己的记忆时,我们可能会认为这是必要的。
由于黏菌爬行过的地方都会留下黏液痕迹,因此这种潜在记忆并非留下线索的黏菌先前学习的结果。如果这一假设成立,那么绒泡菌对细胞外黏液的利用就提供了一个无需学习的记忆的重要例子——外部记忆痕迹不是通过留下痕迹的个体的学习形成的。绒泡菌还以另一种方式展现无需学习的记忆——内部记忆痕迹是在使用它的个体没有学习的情况下获得的。为了了解其中的原理,让我们转而考虑绒泡菌的栖息学习和内化记忆存储的一个例子,这是后一种无需学习的记忆的基础。生物学家 Romain Boisseau 领导的一项实验就很能说明问题。
幼稚细胞无需通过直接接触盐而形成习惯,就能获得记忆
2016年,布瓦索及其同事证明,在反复将一个原肠细胞放置在琼脂桥的一端,并在其和食物源之间放置少量厌恶刺激物(奎宁)后,经过训练的黏菌会开始更快地接近食物源,并忽略厌恶刺激物。这种对重复接触同一刺激的反应减弱,首次为绒泡菌能够进行习惯化学习提供了清晰的证据。与绒泡菌对细胞外黏液的利用一样,这个例子涉及一种非陈述性记忆——通过行为表达的记忆,无需经过有意识的反思或回忆——但它关注的不是非陈述性空间记忆,而是对厌恶刺激的耐受性。
似乎这还不够令人印象深刻,后来的研究表明,黏菌甚至可以将记忆从一个个体转移到另一个个体。在2016年的一项后续研究中,大卫·沃格尔和奥黛丽·杜苏图尔发现,一个幼稚的、未经训练的绒泡菌细胞,在与一个已适应并经过训练的细胞短暂融合后,会对盐——一种厌恶刺激——表现出相同的适应性反应。重要的是,即使在两个细胞分离后,幼稚细胞仍然表现出这种反应,它会更快地接近位于含有驱盐剂的桥末端的食物源。换句话说,幼稚细胞获得了记忆,而无需通过直接接触盐而适应。
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这段记忆属于谁?与记忆形成一样,我认为,在转移记忆的情况下,它属于使用该痕迹的原体细胞,因为它的行为受该痕迹引导。现在,我们可以证明,无需学习,这两种记忆类型都适用这一观点。如果记忆是一种受自然选择影响的生物性状,那么选择主要作用于那些通过使用记忆痕迹获得适应性优势的生物体。即便如此,由于亲缘关系密切的原体经常合并形成更大的细胞,在某些情况下,记忆使用带来的好处也可能间接延伸到最初的细胞外黏液生产者。例如,如果生产者后来与记忆使用者合并,它可能会因为记忆使用者之前的觅食效率(即营养充足)而获得适应性优势。因此,在进化的时间尺度上,选择可能不仅作用于使用粘液痕迹作为记忆的能力,还作用于在其中留下化学信息的倾向,使得它们更容易被亲属识别,特别是如果这确实有利于相关细胞的适应性。
秒那么,黏菌能教会我们什么关于生物记忆的知识呢?其中一个教训是,空间记忆不必完全局限于生物体内部(就像HEC那样)。此外,被利用后成为记忆痕迹的东西(例如细胞外黏液)不一定是外部痕迹产生者学习的结果。另一个启示是,在某些情况下,个体无需参与学习本身即可获得这种记忆。这引出了人类案例中一个有趣的相似之处。毕竟,我们确实会定期阅读他人编写的说明、地图和手册并采取行动,借鉴他们通过经验而非自身经验获得的信息。尽管这些外部化的信息来源通常具有陈述性结构——旨在明确地表述事实——但我们经常会自动地根据它们采取行动,而无需有意识地回忆或反思它们所传达的信息。通过这种方式,它们以功能上类似于非陈述性记忆的方式指导行为。虽然这种类比不应被过分夸大,但人类和黏菌的例子都说明了记忆如何与个体学习脱钩,而是通过环境结构为他人所获取。
当然,这些结论在传统认知科学和心理学领域仍然存在争议,因为记忆通常被定义为记忆拥有者学习的结果。尽管弗朗西斯·克里克等人在1984年提出了重要的担忧,但记忆存储仍然常常归因于突触可塑性——神经元之间连接强度的变化——这消除了外部记忆痕迹的可能性。话虽如此,一些人,比如心理学家C·兰迪·加利斯特尔——他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记忆也可能存储在大脑中的RNA等分子中——仍然保持着跳出固有思维的警惕。然而,鉴于越来越多的经验证据表明,像绒泡菌这样的非神经元生物也表现出记忆引导行为,即使这种跳出固有思维的思维方式仍然根深蒂固地植根于关于大脑记忆要求的传统观点,而HEC认为的那种严格的内在主义并非总是如此。 HEC 和无需学习的记忆都不是容易接受的药丸,但话说回来,非神经元生物能够学习的想法本身也并非易事——而绒泡菌的 行为似乎明确地支持了这一想法。
无论是在实验室(或在爱丁堡公寓狭小的书房)进行的实验,还是基于经验的空谈哲学,绒泡菌都提供了一种宝贵的模型生物,用于检验、挑战和改进我们的一些最基本的生物学概念,例如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