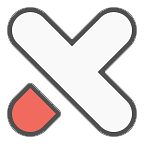牛津大学语言哲学家JL·奥斯汀于1960年2月8日去世,仅仅几个月前,他就收到了“严重”的诊断结果。他的朋友以赛亚·伯林称这是一个“死秘密”——奥斯汀本人也“不知道”自己所剩的时间不多了。随着希拉里学期的临近,奥斯汀只申请了四周的休假,直到他的腺体“恢复正常”。五周后,他去世了。
如今,奥斯汀最为人熟知的,是他的言语行为理论。该理论认为,语言不仅仅是传递信息,更能执行行动。简而言之,我们用语言来做事 。然而,奥斯汀晚年的信件中却少了一个词——癌症。肺癌,这个对奥斯汀来说“极其严重的”诊断,在48岁时夺走了他的生命。
和当时的许多人一样,奥斯汀的医生、家人和朋友都避而不谈他的疾病。“癌症”这个词在当时只是悄悄话,是一个禁忌,可怕到难以启齿。医生们通常不愿透露诊断结果,担心仅仅说出这个诊断就会断送一切希望,加速死亡。正如一位作家所言:
癌症患者之所以被欺骗,不仅是因为这种疾病(或被认为是)意味着死亡,还因为它被认为是淫秽的——这个词的本义是:不祥的、可恶的、令人厌恶的。
那位作家——苏珊·桑塔格——和奥斯汀一样,敏锐地观察到了语言的力量。在《疾病的隐喻》(1978)一书中, 桑塔格揭示了围绕疾病(尤其是癌症)的隐喻不仅仅是描述;它们塑造了人们的认知,强化了污名,并强加了可能造成伤害的叙事。她呼吁人们从这些隐喻中“解放”出来,认为我们必须停止将癌症视为“邪恶的、无敌的捕食者”。
秒昂塔格于2004年因癌症去世。那时,叙事已经发生了变化。1975年她首次被诊断出患有乳腺癌时,还没有粉红丝带或呼吁早期发现和治疗的广告。然而,到她去世时,癌症已从私人疾病转变为公众运动。女性团结游行;男人们为“胡子十一月”(Movember)留起了胡子;运动员们穿上了粉红色的运动衫,而彩色腕带则代表着对从白血病到胰腺癌等各种疾病的支持。
癌症不再是一个可耻的话题,而是一个战斗口号。打破沉默无疑是一种进步。但这种转变也带来了新的比喻——以及新的期待。癌症不再是一种不可言喻的命运,而是一场需要奋战的战斗,患者被视为战士,被号召“拼死一搏”。驱车穿过美国任何一座大城市,你都会看到写着“我们为你而战”和“你的战斗从这里开始”的口号的广告牌。癌症治疗中心招募患者,敦促他们参军。公共卫生运动呼吁人们时刻警惕潜伏的敌人,并在其扎根之前将其消灭。曾经令人恐惧、难以言表的癌症,如今已成为行动的号召。
如今,许多人担心这种局面已经失控。过度治疗——在不太可能奏效、甚至可能造成损害的地方进行干预——已成为现代肿瘤学的一个主要问题。以前列腺癌为例。仅在美国,每年就有超过5万名男性被诊断出患有低风险前列腺癌。这些癌症很少扩散,观察是一种安全的方法,其疗效与手术或放疗相当。然而,超过一半的患者仍在接受激进治疗,冒着尿失禁、阳痿和其他危害的风险,而且没有明显的疗效。
我们治疗不是因为它有帮助,而是因为另一种选择就像放弃
类似的模式也出现在其他癌症中。美国每年有超过5万名女性被诊断出患有导管原位癌(DCIS),这是一种进展风险较低的非侵入性乳腺癌。然而,几乎所有患者都接受了手术,其中三分之一的患者接受了乳房切除术。试验表明,观察治疗可能是一种安全的替代方案,但招募患者却举步维艰——即使招募到了,许多人也转而接受手术治疗。正如一位评论员所指出的,临床医生习惯于采取行动,而患者则“从小就被灌输‘癌症’被切除的观念”。
但过度治疗并不止于早期疾病。据估计,美国有近70万人身患晚期癌症。对许多人来说,生命的最后阶段将以干预为标志。三分之一的人会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接受积极治疗,五分之一的人会在生命的最后几周接受化疗。这些治疗很少能延长生命,而且几乎总是会降低生命质量,带来疲惫、恶心、住院和与亲人失去相处的时间。尽管指导方针不鼓励这种做法,但人们仍然默认采取行动。我们治疗不是因为它有帮助——而是因为不这样做就感觉像是放弃。
作为一名医生,我亲眼目睹了这一切。患者听到“癌症”这个词,就做好了战斗的准备。有些人告诉我,只要能摆脱癌症,他们什么都愿意接受——无论多么有害。即使证据支持观察和等待,这种想法本身就让人感觉像是投降。即使证据支持姑息治疗,许多人仍然选择“战斗到底”。引用一位患者的话:“无所作为别无选择。 ”临床医生也感受到了介入的压力。这种紧迫感并非来自疾病生物学,而是来自话语的分量。
正因如此,一些肿瘤学家现在主张我们应该放弃“可怕的癌症”:将早期乳腺癌和前列腺癌等低风险病例的癌症标签去除,可以让患者免于不必要的治疗。我们又回到了原点——但原因却截然相反。奥斯汀的医生们为了保留希望而隐瞒的事情,如今的肿瘤学家也会为了防止我们过度治疗而隐瞒。这或许是一个解决严重问题的诱人方案。癌症过度治疗每年损害数百万人的利益,并耗费医疗系统数十亿美元的资金。但重新命名真的是答案吗?
T为了解开这个谜团,我们可以转向奥斯汀和他的言语行为理论。想象一下,你被诊断出患有一种疾病。起初是脚趾甲发黄。医生检查后说:“你患有X疾病。”她解释说,这种疾病生长缓慢,但可能会扩散。虽然有治疗方法,但有副作用。她说,有些病人选择与X疾病共存。你考虑了各种选择,选择了治疗,然后痊愈了。你再也不会想起X疾病了。
现在想象一下另一种诊断。这次诊断始于你腹股沟的一个肿块。医生做了一些检查,然后告诉你:“你得了Y病。”听到这几个字,你不禁打了个寒颤。她试图安慰你:这种病生长缓慢,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扩散。这种治疗方法有副作用。但她补充说,许多患者发现与Y病共存很艰难。她把你介绍到一个互助小组,在那里你听说了一些与Y病抗争并最终取得胜利的患者。你选择接受治疗,病情得到缓解。你仍然是Y病社区的活跃成员。你认为自己是Y病的幸存者。
X疾病和Y疾病之间有什么区别?甲癣(一种趾甲真菌感染)和惰性淋巴瘤(一种生长缓慢的淋巴结癌)之间有什么区别?没错,它们的预后不同。但或许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其他地方。它在于奥斯汀所说的“言外之力”。
言外之力指的是言语本身所产生的力量——它创造承诺,重塑角色,影响身份认同。以“我保证”为例:这两个词不仅表达了一种意图,还创造了一种义务。或者以“你有罪”为例。如果这句话出自法官之口,它不仅会指责你,还会使你成为罪犯。
战斗机效应是过度治疗的强大驱动力
同样,“你得了癌症”这句话不仅仅是陈述一个医学事实。癌症诊断就像有罪判决一样,具有特殊的言外之力。它不仅仅是描述一种病症;它还赋予了你一个新的身份。简而言之,它让你成为了一名癌症患者。
不仅仅是一位患者,更是一位斗士。“战胜癌症”。“拼尽全力”。这些口号不仅鼓舞人心,更具有指导意义。它们设定了期望:展现力量,而非软弱;决心,而非消极;坚持,而非投降;行动,而非无所作为。癌症不仅仅是一种诊断,更是一声战斗的号角。我们可以给这种特殊的言外之力起个名字。我们称之为斗士效应。
“斗士效应”是过度治疗的强大驱动力。它导致低风险前列腺癌患者接受不必要的前列腺切除术。它促使患有惰性乳腺病变的女性接受可能并不需要的乳房切除术。它促使晚期患者在临终之际,用宝贵的时间去换取无效的治疗。“癌症”这个词需要行动。用一位患者的话来说:“必须有所行动。”
认识到癌症的言外之力,让我们聚焦于两种应对过度治疗的相互竞争的策略:重新命名与重新构建。重新命名的支持者——那些主张我们应该放弃“可怕的癌症”这个词,干脆用其他词来称呼早期癌症的人——专注于阻止癌症言外之力的直接影响。通过不说“癌症”这个词,他们旨在阻止“斗士效应”的发生。
但这有点像修建水坝来阻止洪水泛滥。它或许能保护一些地区,但却无法解决水位上涨的根源。驱动过度治疗的社会和文化潮流依然存在,随时可能再次汹涌澎湃。要真正解决过度治疗问题,我们需要采取不同的策略。与其在地方修建水坝,不如平息水位上涨。与其重新定义诊断,不如重新定义它的力量。
T重新定义癌症的言外之力,意味着改变赋予该词力量的语言和社会实践。它摒弃了“癌症需要抗争”的论调,旨在化解——而非仅仅阻止——癌症的言外之力。它为治疗决策创造了空间,使其由风险、益处和患者偏好而非好斗的期望来指导。
为什么要重新定义而不是简单地重新命名?至少有三个令人信服的理由。首先,重新定义针对的是过度治疗的根本原因。研究表明,用像IDLE(“惰性上皮来源的病变”)这样的术语重新命名早期癌症,可能会减少选择不必要治疗的患者。但这就像试图用一个朗朗上口的缩写词——比如BIBBLES(“真正经长期验证的安全性的生物免疫增强剂”)——来简单地取代“疫苗”一词来解决疫苗犹豫问题一样。 显然,这只是回避了问题。重新命名或许可以在某种情况下阻止过度治疗,但它却保留了潜在的误解:所有癌症,无论风险如何,都必须积极治疗。
更重要的是,重新命名不仅不会让误解消失,反而会强化它。避免使用“癌症”一词只会助长奥斯汀医生们持有的、桑塔格批评的那种说法:癌症太可怕了,不该被提及。正如称呼伏地魔为“那个连名字都不能提的人”只会加深他的恶名一样,避免使用“癌症”这个词只会巩固癌症的威力。重新命名某些癌症,同时将“抗争”一词保留给那些被认为合适的情况,最终强化了人们应对过度治疗的努力所应挑战的期望。
重新构建旨在改变诊断的规范和期望
选择重新构建的第二个原因是,它尊重患者的自主权。想象一下,你有个美国朋友艾米,她讨厌西葫芦。她并非过敏或不耐受,只是担心吃西葫芦会生病。你担心艾米错过西葫芦的美味,于是准备了你最拿手的蔬菜杂烩。知道她讨厌西葫芦,你策略性地告诉她,你的蔬菜杂烩是用“courgette”(西葫芦)做的。(艾米学的是美式英语,不熟悉西葫芦的英式同义词。)她吃了你的蔬菜杂烩。
在这种情况下,你显然欺骗了艾米。你阻止了她根据自己的喜好自主决定是否吃你的蔬菜杂烩。即使你认为她的恐惧毫无根据,你的欺骗也是不合理的。一个更好的朋友应该帮助艾米明白西葫芦不会对她造成伤害,这样她就可以放心地享用这种蔬菜了。
重新定义的目的正是如此:它直接解决恐惧,帮助艾米看清西葫芦的真面目。相比之下,重新命名会让艾米吃“西葫芦”。如果她是你四岁的女儿,这可能还算合适,但对你的朋友来说就不合适了。
批评人士认为,重新命名早期癌症是家长式作风,侵犯了患者自主决策的权利。公众也表达了同样的担忧,担心重新命名会让人感觉像是在欺骗。尽管家长式作风在现代医学中理所当然地敲响了警钟,但有时也并非毫无道理。支持重新命名的人辩解说,这是一种让患者免受“癌症”一词带来的情感负担,促使他们做出更好选择的方式。然而,这种方法最终存在缺陷。它承认“斗士效应”存在问题,但却无力解决。结果,那些病情仍然被标记为“癌症”的患者仍然会受到“癌症”的全面影响,被迫采取过于激进的干预措施。
重新定义提供了一条更好的途径。它并非回避问题,而是试图改变围绕诊断的规范和期望。如此一来,它尊重了患者的自主权——赋予所有患者自主做出明智、合理的治疗决定的权力。
当患者发现他们所谓的“病变”曾经被称为癌症时,信任就会受到侵蚀
选择重构的第三个原因是它更加稳健。我所说的稳健,是指它能够抵御医疗实践、检测制度和人类行为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可能会削弱遏制过度治疗的努力。
以癌症筛查为例。最近,为防止过度诊断和过度治疗,将乳房X光检查限制在50岁以上女性的尝试引发了广泛争议,包括相互矛盾的指导方针、专业争议和媒体的喧嚣——这场争论被称为“乳房X光检查之战”。即使采用了限制性筛查指南,由于个人偏见和患者压力的影响,患者的依从性也参差不齐。与此同时,血液癌症检测等新兴技术为过度诊断开辟了新的途径,进一步加剧了解决过度治疗问题的难度。
重新命名似乎更为有效:如果我们无法阻止医生发现无需治疗的早期癌症,至少可以改变它们的名称。用“病变”或“IDLE”代替“癌症”或许可以规避“战斗机效应”,从而减少不必要的干预。但这种策略同样脆弱。任何医生都知道,而且我在自己的实践中也屡见不鲜,这种委婉的说法不可避免地会引发更深层次的问题。借用1960年电影《十一罗汉》中的一句台词:“医生,你看,说清楚点。这是大赌场吗?”
此外,当患者发现他们所谓的“病变”曾经被称为癌症时,信任就会瓦解。而且,在发现的那一刻,“西葫芦”这个词的全部言外之力又会再次出现——而且往往带着一种强烈的报复性。当艾米在谷歌上搜索“西葫芦”时,她肯定不会高兴。
重新定义是一个更强有力的解决方案。它不再依赖脆弱的委婉说法,而是直接挑战“斗士效应”——驱动过度治疗的潜在社会力量。它并非围绕标签展开斗争,而是旨在彻底改变我们思考和谈论癌症的方式。
碳改变我们思考和谈论癌症的方式似乎是一个崇高的目标,甚至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但正如奥斯汀学者所指出的,言外之力并非一成不变。它们受到社会习俗的塑造和维系。承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社会强制要求人们信守承诺。有罪判决的意义在于法律、制度以及社会对犯罪的看法。这些并非一成不变。改变是可能的。
癌症诊断也是如此。转变言外之力意味着改变赋予其力量的惯例——不再将每一种癌症都视为一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打赢的战斗,而是将其视为与其他疾病一样对待,在治疗决策中,需要仔细考虑患者的偏好以及不同治疗方案的风险和益处。这种转变需要多方面行动。医生必须重新思考他们呈现诊断的方式,用强调患者自主性的语言取代军事化的隐喻。公共卫生运动必须超越好斗的形象,精心设计信息,使其具有指导性和赋权性,而不是诉诸恐惧来驱动决策。癌症中心、研究机构和媒体机构都应在消除助长“斗士效应”的规范方面发挥作用。
自桑塔格以来,许多人都在呼吁这样的改变。奥斯汀的洞见为这些呼吁提供了新的清晰解释,向我们展示了改变发生的原因和方式。将癌症诊断视为一种具有强大言外之力的言语行为——能够塑造规范、期望甚至身份——揭示了过度治疗不能仅仅通过重新命名特定癌症来遏制。过度治疗不仅仅是一个医学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和文化问题。要改变我们治疗癌症的方式,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围绕诊断的言外之力。
桑塔格本人对此看得清清楚楚。她甚至亲身经历了这股力量的一次重要转变。夺走奥斯汀生命的那个难以言喻的“严重”诊断,在夺走桑塔格生命之前,已经变得可以言说、可见——甚至公开。这算是一种进步,但这并不是她所期盼的解放。
太多患者认为停止治疗或选择姑息治疗就意味着放弃
她曾尖锐地批判癌症早期给人以沉默与绝望的隐喻,但如今也未能免受其新隐喻的影响。正如她的儿子大卫·里夫在其回忆录《游弋于死亡之海》(2008)中所述,确诊后,桑塔格成为了“积极倡导更多而非更少治疗”的宣传者,推行极其激进的治疗方案——先是治疗乳腺癌,后来又治疗了随后的白血病。尽管“少即是多”的理念体现了她的艺术敏感性,但里夫写道:“在癌症治疗方面,多多益善。”以今天的标准来看,她接受的许多治疗都算得上过度——其毒性很可能导致了她最终死于第二次癌症。
即使骨髓移植失败后,桑塔格仍拒绝放弃。她决心“战斗到最后一刻”,拒绝任何姑息治疗的言论,并敦促医生继续治疗。正如她儿子动情地回忆的那样,这“并非轻松的死亡”——而是缓慢而痛苦的终结,“尊严被剥夺”,“无法接受自身的消亡”。
作为一名治疗血癌患者的医生,我目睹了太多患者仍然面临类似的命运,他们坚信停止治疗、选择姑息治疗,甚至死亡本身,都意味着投降。正如一位晚期癌症患者所说:“如果我死了——这很有可能——那我就是个失败者,我软弱无力,不是一个好的斗士。”
隐喻已然改变,但它们的力量却永存。尽管污名化已被口号所取代,但真正的解放意味着彻底摆脱这些叙事。这意味着重新定义癌症的言外之力,使其不再是死刑判决或战斗口号,而是一种诊断——一种像其他任何诊断一样,需要深思熟虑,而非默认采取行动的诊断。
我们都应该自由地赋予疾病经历以自己的意义
这并不是否认癌症诊断可能带来毁灭性的打击。“你得了癌症”这句话 往往预示着未来将面临改变人生的挑战。癌症仍然是死亡的主要原因,夺走了太多人的生命——其中许多人比桑塔格,甚至比奥斯汀还要年轻,奥斯汀对文学和哲学的不朽贡献也因癌症而悲惨地戛然而止。早期发现和有效治疗——遗憾的是,奥斯汀无法获得这种治疗,桑塔格最终也未能成功——能够而且确实挽救生命。
然而,即使治疗方法取得了进展,大多数癌症仍然难以治愈,治疗过程漫长而艰辛。面对这些困境,有些人或许会将“斗士效应”视为力量的源泉,帮助他们熬过艰难的治疗周期或寻求早期干预。有些患者可能选择接受“斗士”的身份;有些患者则选择“旅行者”的身份;还有些患者则选择完全不同的身份。我们都应该自由地赋予疾病体验以自己的意义。
主张重新定义癌症的言外之力,并非否认疾病的严重性、早期治疗的益处或患者面临的困境。而是质疑“抗争”的期望是否应该融入癌症诊断本身。患者已经在努力做出复杂的决定——探索治疗方案、权衡副作用,并思考这一切意味着什么。他们不应该因为言语的力量而承受“抗争”的压力。将“抗争者效应”与癌症诊断分离,可以让患者做出明智的选择——权衡风险和收益,而不是言语的选择。只有改变这些规范,我们才能实现桑塔格所设想的那种解放——这是真正“去神秘化”癌症的唯一途径,让患者能够自由地塑造自己的身份和经历。
正如奥斯汀提醒我们的那样,我们用语言行事。语言拥有创造规范、建立期望和塑造身份的力量。这种力量根植于语言和社会习俗——正如奥斯汀和桑塔格所熟知的,这些习俗从未固定不变。在奥斯汀的时代,癌症是一种无法言喻的诊断;而在桑塔格的时代,它却成了战斗的呐喊。他们都被各自时代的语言所塑造,并以不同的方式承受着时代的重压。
今天,我们处在一个不同的时刻。癌症患者无需默默忍受痛苦,但他们也不应该被召唤去战斗。如果我们要发扬奥斯汀的洞见,实现桑塔格的愿景,我们不仅要改变“癌症”一词的音量,更要改变其力量。它不应该被低声细语,也不应该被大声疾呼。它应该被清晰而平静地表达出来——这样患者才能自主地面对癌症诊断,不受期望的束缚。为了真正解决过度治疗问题,我们不应该回避“癌症”这个词。我们应该改变它的含义。